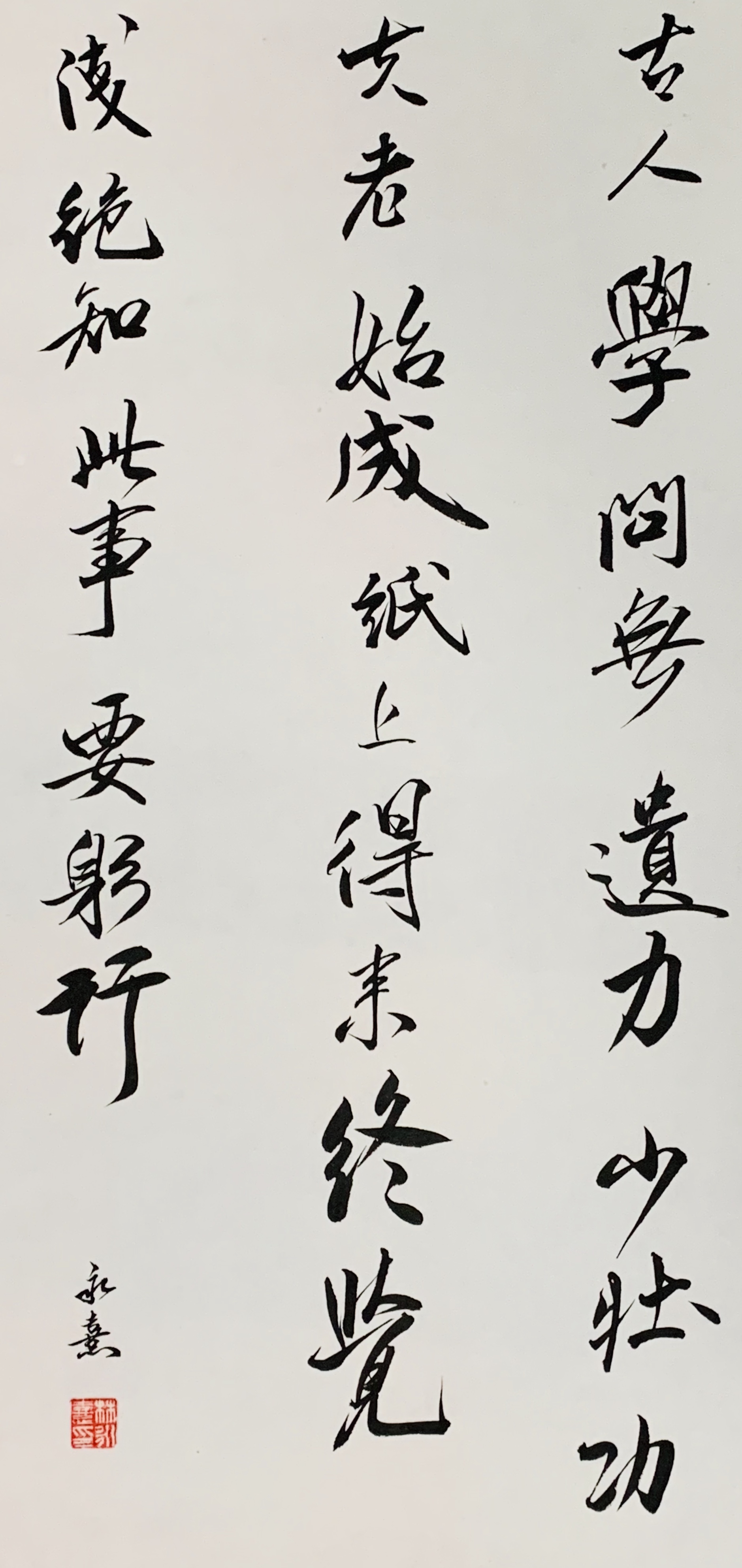死去的风拂过马加丹的海岸。
列夫呛着咳了两下,于是他左手摸向口袋里的小铁壶,但迟疑下又缩了回来,最后他右手压着左手,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身下的栏杆上。
时间还早,还是省一点吧。
面前的海一直在随着风翻腾。翻腾的靛蓝和静止的灰白在视线末端融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列夫眼中渐渐模糊。
这里就是这个球形世界的尽头。而他要在这里等待的客人将会从尽头的另一边现身。
这是无谓的等待,他早该想到的。早几刻钟前他就能躺到沙发上了,但这不是他。等待客人的到来,这是他的礼仪。
天空中全是云,他的眼睛游荡着寻找可以辨别的形状。但是它们太密太厚了,在他尝试沉入想象时,云海立刻把他推了出来。
或许应该来一口。就一口。
拧开壶盖,他先像一位专业品酒师一样,深吸了一口挥发的酒气。
这种辛辣是生命的真正形状。
这一口是很大的一口,他闭上嘴以后马上打了一个长嗝,但是他用袖子遮住然后咽了回去。
生命绝对不能浪费一丝一毫。
盖上壶盖,摇着已经没多少声响了。但燃烧的感觉也开始从胃中蔓延开来,蔓延到整个身体。于是列夫从栏杆上拉起身子,摇着胳膊转圈活动身体。
这还能顶上一会,只能希望客人的船快一点。
无止尽的海浪声让身上的暖意又消降下去。于是他清清嗓子,深吸了两口湿冷的空气,然后哼了起来。
“我们有一个平凡的愿望,我们的愿望就是这样,愿,嗝,愿,愿,呃……”
“只要我还能行走,只要我还能行,嗝,看见,只要我还能呼吸,我就不停冲向,嗝——”
有个巴掌拍了他背好一下,让他把这口气硬是咽了下去,然后打了很长一个嗝。转身缓过神来他立马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因为面前已经站了好大一群人。伸手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不比列夫矮多少,西装背头和油腻的脸,他肯定就是一家之主。
“你是列夫?抱歉让你在这里等候我们,但是……”
他身后的人形形色色,有长有幼。人群远端的几个人转身看着夜空下的海,近处的几个低头或是看着列夫。但在匆匆一瞥下他们的脸庞在列夫眼中都是彻底模糊的。他只能看见彻头彻尾的嫌恶。
“……时间已经不早了,按照旅程安排现在我们应该在餐馆。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列夫脸上的肌肉尝试挤掉微醺,摆出一副职业的微笑。他吐字的口音与对方一般无二。
“了解了,尊贵的先生,对于浪费您的时间我感到非常抱歉。现在,请您与您的家人们移步我们预定中的餐厅。”
沉默中,列夫带领着一长串杂乱的脚步声沿着海岸向前。转角处他下意识回头,但是那个西装中年人身后紧跟着的脸庞年轻的家伙恶狠狠地把他瞪了回去。
或许他们非常不喜欢我的歌喉,就像不喜欢我脑子里的东西一样。
在阳台上列夫独自一人站着。面前的海和前几个小时所见的海仿佛一模一样,一切的不同和变化在百无聊赖的脑海中总会化为和原来无二的一副图景。这幅画叫,等待的列夫?
他转身尝试听玻璃门后的热闹的对话。如果有任何人能看到这个虎背熊腰的身影压低头粘在玻璃门上,肯定免不了鄙视小丑式的眼神。但是在门这边完全寂静的世界中没有这样一双眼睛。
“……他是个将军!爷爷你是最厉害的将军,你说他是不是也是个厉害将军!”这是一个稚嫩的声音。
“将军!没有什么将军!哪来那么多将军。从我离开这里到今天,这里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今天这里只有一位将军,将军是小甜心你!别说了,吃点……”
列夫抽开了注意力。那个嗓音,那个老发条绞转着尝试变得甜腻的感觉,令他作呕。他用手握拳重重地击打在胸口,想要从肺中咳出什么东西,但是干咳了几下都没有什么。
深吸着气,他抬头望向天空。
他所妄想的并没有发生。
死去的风依然吹拂着马加丹的海岸。